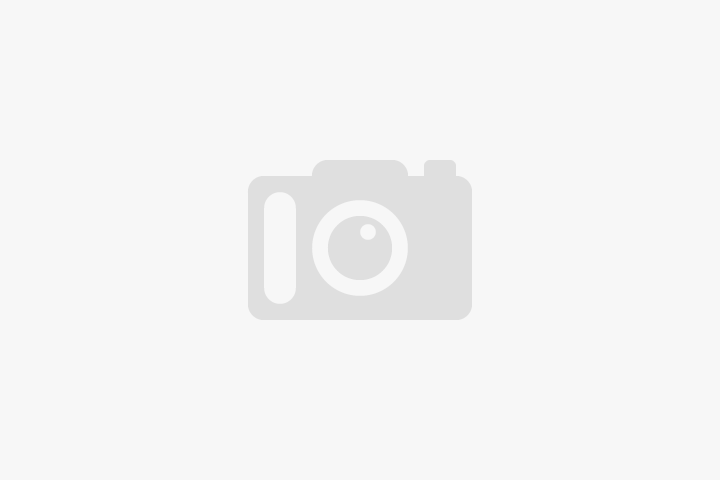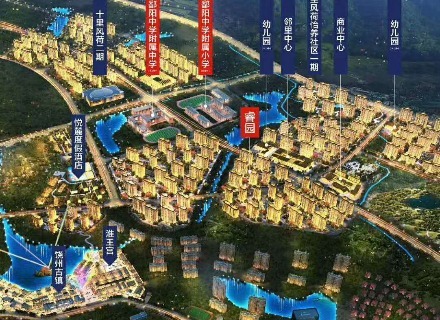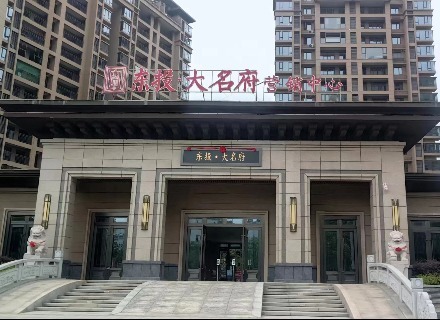微信扫一扫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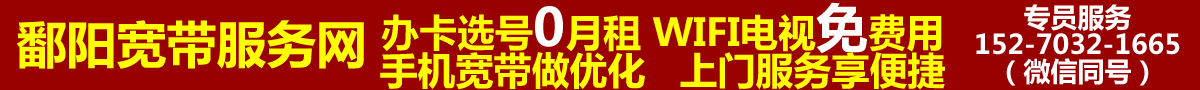
【名家写名湖】刘华:好戏的鄱阳

02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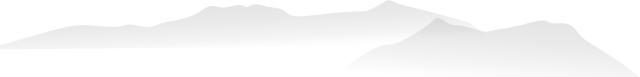
好戏的鄱阳
刘华

鄱阳有个地方叫莲荷国。这名字听上去大气,看过去美丽。接天莲叶的国度,映日荷花的疆域。流连其间,我竟摄下两座仿古新戏台。一座,建筑在莲叶之上,像蹲伏着一片蛙鸣;另一座,仿佛莲蓬,荷花绽放,它便露脸了,还有些娇羞的样子。
戏台后面的一幢幢农舍新崭崭的,却也是空荡荡的。只见一位女子在自家阳台上晾晒,听得一声吆喝,她便躲闪进屋去了。也许退场隐没于弥漫的馨香中。那村庄四周荷花,她乃起舞凡间、入戏太深的花仙子,怕也未必。
莲荷簇拥着的新戏台,引出一个耐人寻味的新话题。朋友告诉我,如今鄱阳乡间兴起建造戏台热,全县共有戏台746座,除了明清时期及以后的38座老戏台,其余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所建的新戏台,建设资金均由村民集资和乡贤能人捐资。我大吃一惊。村庄不是“空心”了么?在这样的背景下,“戏台热”反映了怎样的乡村生活现实和心理现实?

其时为2018年。此后我再次造访鄱阳,得知戏台数量持续上涨不断翻新。现在,此刻,已达千余座了。或许仍有在建的呢。
我对鄱阳的好戏,早有耳闻。鄱阳人好的是饶河戏,此乃赣剧的重要流派,它是在南戏和弋阳腔的基础上经改造发展,变一唱众和、锣鼓伴奏、以板击节的高腔,与乱弹等皮黄声腔融汇糅合,所形成的唱腔丰富、剧目众多、乡土气息浓郁的地方戏剧。饶河戏一经问世,即受到鄱阳和饶河流域老百姓的喜爱,从清乾隆时期起,鄱阳乡间演戏看戏之习蔚然成风,不仅庙会、开谱、开台、做寿、婚庆要做戏,秋收后要演太平戏,甚至违犯乡规族规所领受的处罚,往往就是掏钱请戏。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,唱戏的班社长势如水稻如莲荷,其中既有专业的长班、业余的太子班,也有众多自由结合、走村串户“至家表演”的串堂班。而串堂班多为好戏的农民群众所组成,现学现演,游走乡里,过一把戏瘾。我曾读到一段追忆往昔的醉人描写,云:“突然从湖上传来一声‘叫太保,传帐令’的大花唱腔,这略显嘶哑却高亢激越、掩饰不住苍凉的吼唱,令打鱼的父亲他们兴奋了,也不时以吼唱回应。在夜和水的氤氲中,此起彼伏的交流,缩短了陌生与阻隔,冲破了天与湖的黏合,漫撒在浩瀚的彭蠡……”

从前有民谣极言乡人好戏,道:“深夜三更半,村村有戏看,鸡叫天明亮,还有锣鼓响。”关于好戏者的身心享受,则有民谚概括称:“三天不看饶河戏,肚皮发胀鼓闷气。”似乎,看戏能疏肝解郁,补中安神;民谚又云:“一听锣鼓响,嗓子就发痒。”仿佛,看戏可升举阳气,开心益智;民谚还说:“听过饶河戏,全身长力气。”无疑,看戏将滋补强壮,扶正培本。
既然有许多好处,那么,约吧,看乡戏去!冬月初十夜,我等匆匆应付肚腹之饥,拔腿便走,赶往正在演戏的董家坪村。董家坪在茫茫夜色的深处,在静静昌江的对岸,在记忆犹新的夏天——其时,它及其所属的昌洲乡漂浮于一片汪洋,像一艘吃水很深的船,沉重而缓慢地行走在举世关注的目光里,一连多少天,总也驶不出央视30分钟长度的《新闻联播》。而到了岁末,董家坪要唱洪灾过后的第一场大戏了,这也是完成脱贫攻坚的第一场大戏,更何况,它是由老百姓自个儿做主、众人合伙掏钱请的戏!







好戏的鄱阳自然盛产赣剧表演人才,朋友一一数来,省里以及周边好几个赣剧团都有谁谁谁某某某为鄱阳籍,而不少优秀女演员,正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胡瑞华的弟子。高龄的胡老师至今仍热心传艺授业,或为民营剧团担当艺术指导,或为戏友戏迷讲课教学,有会员一二百人并成立演出队的饶河戏戏迷协会,便把胡老师到访当作协会大事张挂上墙以为荣耀。说到胡老师,故事就多了,她是赣剧观众的偶像,鄱阳人的偶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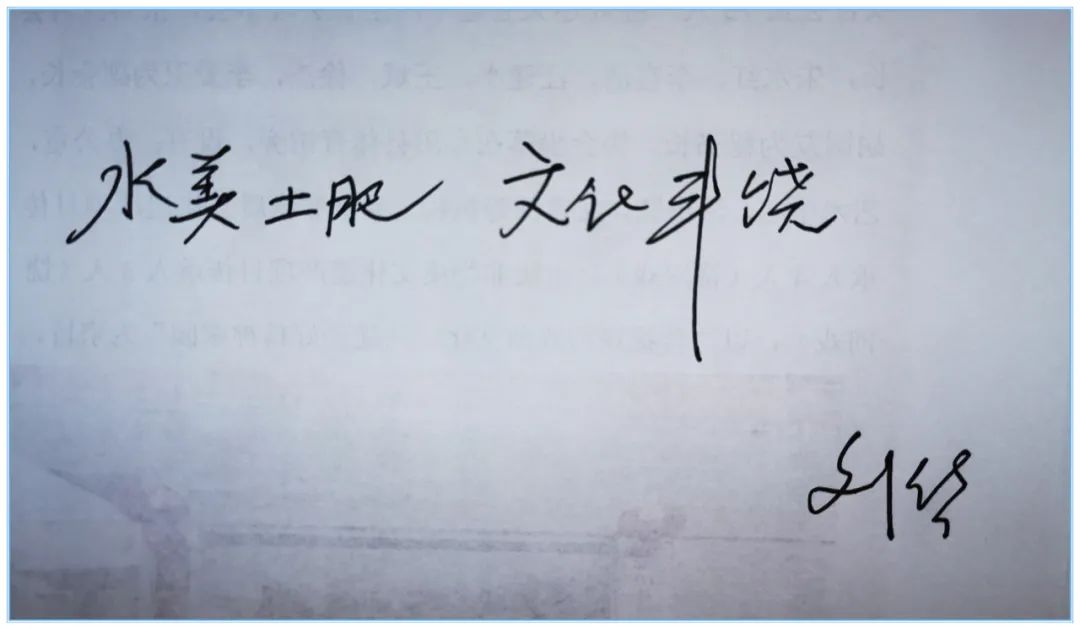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-

鸣山花园
鄱阳县145㎡| 2室1厅 1300元 面议 -

湖城蓝庭
鄱阳县90㎡| 1室1厅 0元 面议 -

湖城馨苑
鄱阳县16㎡| 1室1厅 0元 面议 -

北关前豹子山
鄱阳县40㎡| 2室1厅 450元 面议 -

鸣山花园
鄱阳县150㎡| 3室1厅 1300元 面议 -

先锋小区
鄱阳县130㎡| 0室0厅 1600元 面议 -

瑞阳花苑
鄱阳县120㎡| 3室2厅 1300元 面议 -

中央城
鄱阳县124㎡| 3室1厅 2100元 面议 -

中盛现代城
鄱阳县50㎡| 2室1厅 700元 面议 -

鄱阳县大桥路牢置房
鄱阳县124㎡| 3室1厅 1200元 面议 -

东湖小区
鄱阳县120㎡| 3室2厅 1200元 面议 -

新星丽湖星城
鄱阳县93㎡| 2室2厅 1000元 面议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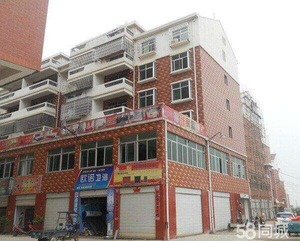
芦田商贸城
98㎡| 3室1厅 26万 面议 -

桃花源纪安澜里
鄱阳县101㎡| 3室1厅 59.99万 面议 -

中央公园小区
鄱阳县116㎡| 3室2厅 78.5万 面议 -

在水一方
鄱阳县105.96㎡| 3室2厅 61万 面议 -

开元时代
鄱阳县113㎡| 3室2厅 68万 面议 -

鄱阳湖城绿洲
鄱阳县106㎡| 3室2厅 78万 面议 -

湖城·新天地商住小区
鄱阳县128.97㎡| 3室2厅 96万 面议 -

中盛现代城
鄱阳县108㎡| 3室2厅 55万 面议 -

中盛现代城
鄱阳县108㎡| 3室2厅 54万 面议 -

东投金麟府
鄱阳县127.6㎡| 3室2厅 0万 面议 -

芝山美林
鄱阳县112.75㎡| 3室2厅 69万 面议 -

世纪阳光小区
鄱阳县40㎡| 1室1厅 24万 面议
-
下一条:鄱阳县金融工作联席会议召开
 微信公众号
微信公众号